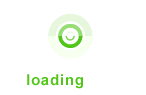这儿是离学校不远的一个桃园的尽头。原是一道河堤.现在水面窄了,果农把河堤向外开辟了几丈种了些葡萄,堤最外边是一排桃树.正值桃花盛开的季节,河堤就像是从桃园飘出的一条花带。
每年的春夏季节,我常常独自来这儿散步。从果农支起的篱笆缝里钻进去,便到了这片宁静自由的天地。
四周一片寂静,只听见鸟儿啁啁的歌唱。我嗅着新鲜的泥土味儿青草味儿,以及桃花的香气,心里有说不出的舒畅。远离了喧嚣的市区,摆脱了案牍劳形的工作,我的心在这静谧的世界无拘无束地欢舞起来。
“这路边矮矮的桃树整日享受这田野的宁静,可愿意我的造访?”
我在一株桃树下站定,树叶子被雨水濯洗得发亮,一簇簇桃花缀满枝头,瞅一眼那娇艳的花朵整个心都充满了甜蜜,深深地吸一口气,五脏六肺都充满了花香.--想我在这小路上徐行,也颇得“小园香径独徘徊”之句了.
不禁想起了崔护的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人面桃花,多么令人向往。只是岁月匆匆,人生能有几个去年?仅几年的光阴,树旁的我,整日为沉重的生活所累,已不复桃花般的容颜了。“桃花依旧,人面不再。桃树啊,假如把你移植到闹市,整日与钢筋水泥灰尘为伍,你该是什么样子呢?”
桃花不语。
我是一个性情沉静的人,到哪儿就象这路边儿的桃树,静静地伫立,悄悄地退居一旁,不夺人耳目。只会透过眼睛默默地去参与,去判断,去描绘。
这缘于我的童年。
自小在乡下长大,家在村子边缘,附近没有小朋友,母亲忙着教书,常常把我一人扔在家里。院子里的一草一木都能激发我的好奇,看到院子里的一排白杨树缀满了穗穗,我心里就叫它毛毛虫。我还用何首乌的根染过塑料布染过小布头儿。家里的狗儿啊猫啊更是我形影不离的伙伴儿。还有那台收音机,是我的宝贝。我总是抱着它,听着“小喇叭”静静地坐在院子里等候着妈妈的归来。后来读到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时,我就立刻联想到我家的园子。那时的我总沉浸在我的小世界里。我,习惯了孤独,也习惯了自由。
初中时,我转到县城第一中学读书。
我依旧孤独,也依旧自由。我是乡下孩子,土气,老师也不重视。那时,我自己安排生活。父亲几乎天天回家。家距县城不过二十里路。中午只匆匆见着父亲一面。我披星戴月地在县城奔波,即便是刮风下雪的日子也无人照应。寂静的夜晚,我独自看书,把父亲办公室里的新华文摘囫囵吞枣地翻看个遍 。我,就象是这路边儿的野草,悄无声息 自由自在地长大。少人关怀,少人呵护。可如今的孩子,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小心地伺候着,好吃好喝地供奉着,怎么还有那么多问题少年?过分的关怀犹如缠绕的茧,虽然温暖却饱受压抑。被束缚的心灵会有多少的创造力?人的成长需要宽松自由的环境。不要把孩子们逼到精神世界的尽头。哲学家说“精神的最高境界是自由”,那么,教育呢?给予被教育者心灵的自由是教育的哪种境界?今天桃园的这份自由宁静给予了我此时丰富的内心世界。
想到这里,我不禁笑自己:避开纷乱的人群,放下琐碎的工作;抖落满身的疲惫,轻松紧张的神经,我不是为自己寻找自由的空间吗?
回校以后,得让孩子们来这里放松放松。
---------
本苑刊登:2001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