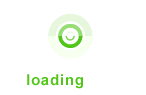从我十五岁离开那始,有十几年,我总是梦回那条路,而每次梦里都是一片恐怖,每次梦醒都心有余悸。有人说:在一切往事中,童年占据着最重要的篇章。童年是灵魂生长的源头。所以,我总是在想,我的童年和少年都在那里度过,我的往事很多都发生在那,我的灵魂也在那里生长起来,离开那这么多年,我为什么老是梦回那条路?我是不是把魂丢在了那里?
从五岁开始,我就生活在那个城郊的农场里,从七岁开始,我就踏上了那条路,每天来往四趟,每走一回得花费我近一个小时,我用我的一双小脚,一步一步踏着,与其说是走,其实更多的时候是在跑,我总是害怕在走进教室前铃声就已经敲响,我总是仿佛听到铃声在我的耳边“叮铃铃”地响,于是,我就努力地快点快点再快一点。就这样,我每天用小脚丈量着这条路。
那条路,来来往往,风里雨里,我整整走过了十年;那条路,不长不短,不宽不窄,长约四五华里;那是一条从郊区走向城市,一条从家里走向学校的路;那条路,有过我的笑语欢声,有过我的痛哭忧伤,陪伴着我走过整个的童年和少年。
那条路属于城乡结合部,从家里一出来,大概有半里,得走过好几道铁路,因为铁路局一个维修站就设在农场里。在集中维修的时候,这里会停靠很多列的火车,有车头、车厢,一节一节的,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些大家伙,于是我们就经常会听到火车的鸣笛声和“卡喳卡喳”的火车开动声。这几道长长的铁路,给过我很多的欢乐,在课余时分和假期里,我们几个小伙伴经常去走铁路,走在一根一根的枕木上,一步跨一根,一根一根地数,或走在铁轨上,伸出手臂,努力平衡身体,比比谁能在上面长得远,走得久。在没有火车维修的时候,这里很安静,我们会顺着铁路走出好远,好象我们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繁华的城市里,那里有我们最美最远的梦想。我们还玩铁路上的石头,那都是清一色的小青石,很结实一个,我们用小青石砸在铁轨上,然后伏下身子,让耳朵贴在铁轨上听它传来的悠扬的声音。这里常年有一道铁路是有车通过的,有一列通往采石场的货车经常在这里来回。所以,每次我们从这里走过时,我们都要仔细地聆听,仔细地看看铁路两头,是不是有火车隆隆的声音,是不是有火车远远地开来。每一次经过那里,我都十分得紧张,好象火车随时都会开过来似的。在我以后十几年的梦里,经常梦见自己站在铁路中央,两头都是轰隆轰隆开过来的火车,它们一步一步地向我紧逼,我惊恐万分,好象是等待宰杀的羊,好象感觉到自己被火车碾碎的疼痛,但是我的脚总是迈不开,无处躲藏。梦醒时,我的心好象还卡在嗓子眼里,往往是一身的冷汗。
走过几道铁路,再走过一段菜地,就到了一片小林子,林子不大,但长着数十株高高大大的板栗树。那不是现在杂交的矮矮的板栗树,而是那种土生土长的板栗树,年纪都很大了,粗粗的树杆我们一个人都抱不过来,而且株株都有几层楼高,伸开着很多很多很长很长的枝桠,浓浓密密的。每当春天板栗树开花时,鹅黄色如絮一般的花,经常飘飘扬扬地落到地上,落到我们的头上,几十株树花儿同时开放,香浓得都能晕倒我们。秋天到来时,板栗树硕果累累,没有来得及采摘的板栗有时候会破壳而出,跌落到地上,草丛中。在放学回家的时候,我们伙伴们有时候会停下脚步,看着高高的树上挂着的果实,馋嘴得不得了,我们看着那些树,就好象詹仰老师告诉过我们的伟人一样。我们还寻找着地上跌落的板栗,仔仔细细地在草丛寻找它们的踪影,偶尔捡到一颗,把它放在地上,用小脚踩上几踩,一点不怕它的刺扎手,剥开就迫不及待地品尝它甜甜的滋味。
但是,在独自一人回家的路上,这片板栗林简直是一道鬼门关,令我毛骨悚然。小时候常听大人们讲鬼的故事,也常常在梦中被鬼吓醒。听大人们说,在这片板栗林中有鬼出现过,比如说哪一棵哪一棵最年老的,都好几十年了,都成精了,在夜黑人静时,鬼就会出来,而且是女鬼。每当我背着沉沉的书包一个人从这片板栗林经过时,我的心总是七上八下没有着落。听大人说,人走路要有精神,不能轻手轻脚的,要稳稳地踩在路上,要用力,要落地有声,那么,鬼就不敢接近我们。于是,每当通过那片林子时,我的眼睛都不敢往四处看,只是死死地盯着前方的路,尽力用小脚跺出最响的声音来,好象在证明自己的勇敢无畏。其实,我心里总是在猜测,哪一棵板栗树是妖怪,我总是在担心着,妖怪会突然从树身中钻出来,把我抱了进去,活活吞了我。在以后的梦中,每次梦到这的时候,都是一片漆黑,阴深深的板栗林好似有一阵阵寒风呼呼吹过,破花乱絮随处飞舞。而我就象是一只孤单可怜的要穿过这片林子的小兔子。我跳一步,就竖起耳朵听一听,瞪大眼睛看一看,但我总是能看到参天的大树里有白色的影子飘来飘去的,忽儿是天宫的仙女,忽儿是地狱的鬼魂,吓得我全身的毫毛都能一根一根地直立起来,简直能把我变成一只刺猬。
穿过板栗林,就走到大道上来了,开始是不宽的泥土路,后来就修成了柏油路,也宽敞了不少。一边是一道一个林业研究中心的高高的围墙,一边是矮矮的茶树林。我们每天沿着这条路走,好象是沿着城市的边沿在行走,因为围墙里的人是城里人,围墙外就是乡下人了。这一段路长长的,还有一个坡。有伙伴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钻到茶树林里找野果子,有野山楂,还有很多不知名的红红的、黄黄的果子,都很诱人。特别是春天到来时,茶树林里会钻出很多很多的映山红,红红的这里一簇那里一簇,我们总是忍不住地去摘它一把,拿在手上,就象是举着鲜艳的红旗,我们还会把一朵一朵的映山红花瓣放到嘴里吃,吃得嘴上红红的,还很甜的。秋天的时候,茶树花也要开了,一朵朵白白的,可爱又漂亮。降霜以后,茶树籽都要成熟采摘了,挂在茶树上沉沉的,茶树枝也都低下了头。特别是一朵朵的茶花,挂满霜雾更是可人,我们经常用空心的稻草杆伸到花瓣丛中,吸取茶花的蜜,很甜很甜的。
这条路对大人来说不长,但这条路有时候对我来说是那么得遥远,好象总也走不到头。在这条路上,充满着我的渴望,我渴望一件花衣裳,渴望一把小花伞,渴望一双小雨鞋,渴望能搭乘一辆便车。小时候家里很穷,我总是穿姐姐穿小了穿旧了的衣服鞋子,每天上学放学,看着来往路上,穿着花花绿绿的花衣裳的小伙伴,心里就渴望呀,渴望什么时候能穿上母亲给我做一件花衣裳。姐姐穿下的小雨鞋让给了我,可是对瘦弱的我来说,那就象两只船。姐姐用旧的小伞让给我,不是小花伞,不是小布伞,而是一把黄色的木柄的老式桐油布伞,笨笨的。每当雨天来了,我撑着重重的难看的桐油布伞,穿着船一样的雨鞋,现在想来,那样子就象小丑一般。那时候,我的心里急呀,我很累,撑伞的小手很累,走路的小脚很笨,只听到脚下是“扑扑”的声音。那哪里是鞋呀,我就象是拖着两条船一样艰难地行走,我多么渴望能有一辆便车载我一程呀。望着同伴们轻盈的脚步,内心的渴望就象火一样地燃烧。在以后的梦里,我经常梦见自己走在这条路上,长长的望不到尽头,姐姐们只留给我一个远远的背影,我在后面想追呀追呀,可是脚就象是栽在了路基里了,一点点也迈不开,急得我心里好象压着铅块一样沉重的东西,透不过气来。
走过那一段路,就走到了城市的街道了,虽然是城市的边缘,但人来人往也开始热闹起来,而且路两边有了很多的店铺了。那里对我充满着无限的诱惑,有各种各样的糖果和糕点,有各式各样的衣裳,有各种色彩的鞋子雨具。我的目光在那里停留过无数遍,我想象着糖果的甜,想象着糕点的香,想象着一件一件的花衣裳穿在自己身上的美,想象着手撑小花伞,脚穿合脚的雨鞋走在路上的轻盈和自豪。但这些,只停留在我的目光里,从来没有出现在我的梦中,不知道是不是我不敢做这样的梦,是不是我知道不管我梦多少遍,这些梦都无法实现,还是老天不想让我对梦有太多的依恋。在这条路上,有我目光中的渴望,更有我目光中的自卑。我除了看路两旁的事物,我很少去看别人的眼,我总是低着头,默默地前行,好象一个人在沉思。没有人会知道,我不喜欢别人的目光在我的身上多停留一会,我不喜欢别人看我黄黄的头发,不喜欢别人看我或大或小,或破或烂的衣裳,不喜欢别人眼里露出的对一个小姑娘的怜惜之光。我不要看他们,我也不要他们看我,我宁愿自己象一个游神,从他们身边走过。
走完这所有的路,我就到了学校了。这样来来回回、反反复复,我一直走到十五岁。当我们举家搬到城里时,我真是做梦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彻夜彻夜地做梦,梦里都是以前的家,梦里都是那条路,轰隆隆的火车向我碾来,鬼魂在我身边晃荡,路漫漫长长,好象我永远永远也走不出,永远永远也走不完。就这样梦了十几年,每次梦醒都是一身冷汗,每次梦醒我都要仔细想想,此刻自己身处在哪里,是不是还在原地?这样的梦太让我恐惧了,梦醒后的晃晃忽忽,让我觉得好象是个丢失了魂魄的人,于是,我又一次一次地重新入梦,好象要找回自己的魂。这么多年,我走过很多的很长的路,唯有那一条路,在我的心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许就这两年吧,不知不觉中,那个梦已经离我远去了,我渐渐地淡忘了那里的一切,好象魂终于又回来了自己的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