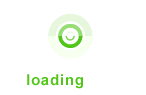我居住的是一套二室一厅的双阳的房子,两个卧室,靠西,靠东各占一地。厅子间二十平米,这在东北来讲,已算比较宽敞了。和大多数的家庭一样,我也把电视、沙发和几盆花摆在厅里,不占地方,也简单明了,再在沙发下养一只跟随我十几年的巴西龟,蹲在角落里探头探脑的,却也觉得有趣、平静、温馨又有一些别致。
当初我买这套房子,完全是从僻静少喧闹考虑的。那时这幢楼属于市区的一个边角,商店没有几家,人也就很少,价格上也就比市中心便宜了许多。但让我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这里成了开发区,商店忽然间似雨后的春笋,一排排快速地长了出来。更让人恼火的是,我居住的这幢楼下新开了一条路,从早到晚,车水马龙,人声鼎沸,打破了我日常平静的读书生活。
如上所说,当初我就是因为这里比较僻静,我才选择了这套并不太让我称心的房子的,我的原意是买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三口人,两间居住,一间做我的书屋。但当时这里的僻静环境动摇了我另选别处的想法,选择了这里,现在鱼和熊掌都没得到,心里不免有些后悔和懊恼;平静打破了,更丢了“书房”。可事已至此,只有另想别的办法来弥补了。
怎样弥补呢?我考虑再三,也就得“就地取材”,从靠西的那间屋子来做文章了;这是一间二十五平米的房间,我把它一分为二,间壁出一间八平米多一点的小房间来,而且,间壁出的这间屋靠着客厅处,也就是说,不临街,不靠窗,独占一处,“曲径通幽”。
这间屋子“建”好后,我把两壁扇墙都摆上了书橱,把全部的书都摆了上去,摆不上的,就堆放在地上,虽然看上去有些零乱,但我喜欢这种乱,使人觉得杂乱中透出一丝宁静。
平常的时候,我的这间屋是不让人进来的。当然,家人也知道我的脾性,也从不进来。那种乱中取静的环境,确实是个读书、写作的好地方。就是不读书,静静地坐在那里,半闭着眼睛,什么也不想,也是一处静心小憩的好地方。平常的日子里,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这间屋子中度过的,除了倦了、乏了,才会走出“书屋”到厅里看会儿电视,侍弄一下花草。
特别是在冬夜的雪天,靠坐在暖气旁,围着大衣,捧着本书,想像着窗外风声裹着雪花发出的“沙沙”声,真有一种蛰居洞天仙府的感受,另一种享受。
有一天,我像平常的时候一样,坐在零乱的书堆中埋头读着书,那个时辰,正是下午,是冬日里一天最冷的时段,盖在我腿上的大衣这时好像也失去了平日的绵厚,显得那样的薄凉,好像外间屋子窗外呼啸的北风,此时都钻进了这间小屋子里来,在屋子的顶端刮来刮去……而这时,我忽然觉得我的膝盖处凉得特殊,是那种彻骨的凉。我觉得诧异,想用手去捂一下,却不知捅到了一个活物——原来是家中的那只老龟,不知何时跑到我这间屋子里避风来了。我知道,老龟此时正在冬眠,一般情况下它会窝在一个地方动也不动的,但为何“窝”到我的 “地界”里来呢?或是想换个环境吧,或是这里更安静。我没有多想,又把它放回了厅子间的沙发底下。
但晚饭的时候,我看见那老龟又从沙发下爬了出来,四平八稳、缓步趋行地朝着我那间小屋走去。怎么住的好好的就搬了家呢?我问爱人。爱人说,这沙发正对着大门,天越来越冷了,它不搬走会受不住这窜堂风的风寒的。噫,原来如此,想必这家伙把这沙发底下看成无人问津的陋巷荒陌了,要徒迁到我那僻静的“城府”中安营扎寨安生冬眠了。
老龟一住在这里就是两年,没有再择新居。我也没有再理会它,由它春天来回亦步亦趋地来回穿梭于两个屋子之间;任它夏日里晒足太阳,带给这小屋中一息阳光味儿;更有深秋时节将要冬眠时困顿的跌跌撞撞的丑态毕出。特别是在不经意间的一抬头,就会看到它项挺抻立侧目圆睁对着你看,是那种目不转睛、静澜如水的看,直让你稍有些许杂念的思绪再一次安宁下来。
现在,我时常站在平台上倚窗观景,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车马,听着高低陈杂的喧闹声,抬起头来观望远方的灯火楼群,耳际响着风声雨声和落雪声,也或在某个下午、傍晚,左首龟,右首茶,对着眼前的纷杂和喧嚣,心中的一切却轻轻地放逐、完全地放逐开来……此情此景此心绪,真是一种卑以自牧的惬意。沉郁中开阔的远翔……
我不再后悔这个曾经给我带来懊恼的居室,我想,我改变不了住所周围的环境,我可以在原有房间的条件下规拢和 “安排”一下它的格局。也或这小小的一点改变,就会让自己整个生存状态、生活态度都会随着自己生活的轨迹运转,并在这其中享受到意想不到的乐趣。
当然,各人居住的条件和生活态度各有不同,喜好也各异,但怎样去生活,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主动的和被动的生活也迥然不同。也或,我的主动,就是你感觉中的被动;你的被动,可能就是我生活中的需要。只是,我们每个人追求的共同目标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快乐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