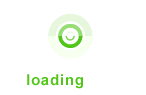东北的三月,季节应该还在残冬里。
那年,我正是在这个季节里从哈尔滨举家来到了这个城市。那天早晨,云乌黑黑的,天上飘着清雪。从大客车上下来后,趁大人们不注意,我扭身向大院门口跑去。刚才在车上,我看到在雪雾中有一大大的古城,还有长长的城墙……
很快,我就跑到了古城墙的大门口;这是一座公园,大门口站着一个和公园大铁门一样铁青着脸的男人。“票?”“没…有……”“去!”我傻了,手却指着铁门里远远的那座城和墙:“我要进去看……”“滚!”那人猛地吼了一句,吓了我一跳。也正在这时,一个瘦小的身影从那人身旁“嗖”地窜进了大门里,速度之快,绝对超过那冷家伙的目光。还没等那冷家伙转身、抬腿,我也“悠”地一下从他的腋下钻进了门里,“快,”远远地那小瘦个儿冲我喊到,“回来,”冷家伙冲着我和那小瘦个儿喊,“去!”小瘦个道,“小崽子,回来,票。”“滚!”小瘦个儿又回道。“小兔崽子,看我追上你泡儿(打)你!”“笨,追不上……”
我就是跟随着小瘦个儿跑到城墙下的。
“哈尔滨,可没有,这样的城…墙。”小瘦个儿说,我们并肩站在高高的城墙下,仰着脸看着乱雪中青灰色的城墙。“怎么,你是女的,也也,从哈尔滨搬来的?”我低头扭脸儿问,而这时,我也看到,一溜鼻涕正从她的鼻孔淌出跃向嘴角,“浠溜”,她狠狠地吸了一下鼻涕:“嗯哪,女的咋地,你是男的还差点没进来呢…(‘浠溜’她又吸了一个鼻涕,)“女的,怎么留男孩子头?”我看了一眼她让风雪吹乱的脏兮兮的头发问。“愿意,咋地吧!”我没敢再多问,跟着她往城墙上爬去。
那天上午,我和“浠溜”(那天我就是这样叫她的,她很痛快地答应着我,竟没有任何异议。)玩遍了城墙,还有一座老大老大的坟包。那天的雪在傍中午的时候下疯了,我们的小腿儿也跑酸了,再也跑不动了,我们拖动着鞋底儿厚厚的积雪走出了公园的大门。
那个守门的铁冷人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留下来的是一个憨态可掬的大雪人,笑眯眯的。
“‘浠溜’,你多大,叫什么?”“我八岁,叫麦穗。”“怎么,你就是麦穗?那个学芭蕾的女孩儿?”麦穗的名字早在一年前我就听母亲说过,说她胳膊腿儿长,被芭蕾舞学校的挑走了。可是,眼前的这个麦穗瘦瘦小小,长着上宽底尖的三角形脑袋,脸上 “魂画魂”(埋汰)不说,还长着一双眯缝眼……
麦穗好像看出我的疑问,用袖子抹了一下鼻涕说: “我就是麦穗,咋地吧。” “不不,不咋地,反正,我不会叫麦……” “可我知道你叫吕培,比我大两岁,是吧?” “我不情愿地点了点头,心想,真倒楣,让这么脏的家伙知道了自己的名字。 “可昨天在火车上,你爸怎么管你叫 ‘小子’?”麦穗又问我。 “去去,你才叫 ‘小子’……”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我去的公园是清朝的一个叫皇太极的皇帝的陵墓;再后来,我就很少看到麦穗了,偶尔看到,也不说话,只是互相看一眼,矜下鼻子,挤下眼,算是打了招呼。
那年的初冬,麦穗被广州军区招了兵,仍是跳芭蕾,隔一年,我也当兵走了,一去多年。再后来,在雪落雪融里,也把我的许多少年和青年往事溶入了深深黑黑的土地里……
去年,我在一份报纸中看到了一个叫麦穗的芭蕾舞老师的采访报道,还配了幅照片,也让我想起了那年初春时的麦穗,但照片中那大眼睛的美丽芭蕾舞老师,怎么也不能让我联系起那个流着鼻涕眯缝眼的麦穗。可是,晚上同是在一档名人采访的电视节目中,就是这个麦穗,却提起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飘雪的春天的早晨, “……在这个城市里,我只住了不到半年,也只有一个童年的伙伴,一个被我叫做 ‘浠溜’的春天的伙伴……我们在一起玩了一个上午,严格说,我们只认识了这么一个上午,后来就没有再在一起玩过……只记得他白白瘦瘦的,总坐在家里,一动不动地脸对着墙发呆,像个小姑娘……正是他去年发表在一本刊物上的一篇<春天的伙伴>的小说,让我想起了我在这个城市中,还有一个童年的伙伴……时光荏苒,也不知道,他还在不在这座城市里……”
“在”,我怎么能不在呢?正是来到这座城市的第一天,我就认识了你,那个在童年的记忆中有些粗陋 ‘埋汰,而此时端坐于我面前,精细瑰丽的漂亮的舞者,让我打开了春天的记忆,使久已冷漠却有些枯窘的心地又泛起了绿色的春意,让那遥远的细雪,再一次把我僵硬的神精,刮的七零八落,使我不得不再一次梳理一下纷杂迟钝的思路,再一次的放飞自己……
只是,你记错了,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流着鼻涕,叫 “浠溜”的孩子,不是我,应该是你麦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