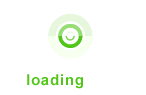类似我这样心理活动远多于外在流露的一类人,大多喜欢用手中的笔记载生活的点滴。我的笔下出现过许多人物,亲人,朋友,老师,同学,甚至天桥上的乞丐,西子湖畔的卖花女和路边补鞋的老者。但是有一个人物我却始终不敢去浓墨重彩,她便是我的母亲。
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对我采取了严厉管教和放任自流相混合的一种极其矛盾的教育方法。她会因为我的一点点小小的过失大发雷霆和絮絮叨叨,她撕过我的作业本,打过我的头,把留长发的男同学当做不良少年赶出过家门,嘲笑过我和同学间关于“人为什么会得神经病”的讨论、说了“我看你就是神经病”这一至今令我难忘的“经典”语句,还因为我爱吃糖“诅咒”过我不满三十岁牙齿会全部烂掉---。
在我眼里她是偏心的,多少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当然她从未承认过),注意力并不在我身上,所以只要表面上看去令她满意,我就尽可以“胡作非为”。8岁的时候我鼓动全班50名孩子孤立一个我不喜欢的女生时她不管,以为我是小孩在闹着玩;10岁时我大夏天穿着厚厚的春秋衫上学她不管,以为我小丫头臭美(实际上我发高烧烧得脸红骨头寒,后来才知道得了疟疾);13岁的时候我连着3天没睡觉、妄图写成一本诗集的时候她不管,以为我在复习功课;15岁时刚开学就丢了化学书、一学期她没见我拿过化学书,但是也从没问过我为什么。好在我有个格外痛惜我的父亲,只要我愿意,所有的失落和不满都能在他那里找到抚慰和排遣。母亲总是对抱我于膝的父亲撇嘴:我看你抱她能抱到多少岁!
1996年3月24日,父亲因病去世。我的世界变得一片黑暗。作家张洁有部怀念母亲的作品叫“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整个春天我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中,对母亲的怨气也在发现她销毁了父亲所有日记那天达到巅峰,我再也看不见父亲的笔迹了。一整夜我的眼睛都像泻洪水的闸门。
而母亲似乎并没有感知这一切,依然常常絮絮叨叨地指责父亲不负责任地“离开”带给她的无穷无尽的痛苦,回忆年轻时独自一人带三个孩子伺候公婆相处妯娌吃的苦受的累经历的屈辱,回忆十多年照顾重病父亲的辛酸。我沉默着,对她的指责不支持,也不反对,但总有一句话堵在心口:这一切都不是父亲愿意的,你又何必怪他?
母亲属虎,又是O型血,这似乎就命中注定了她强烈的个性和气质。她很少能听进别人的意见,除非自己发现真的错了。情绪也总在大喜大悲中起伏,这多少影响了她的心脏和血压的健康。出于做女儿的孝道,我尽力照应着她,生怕出什么闪失。我没有真正清楚过我们彼此之间的感情,每次听到零点乐队声嘶力竭的呐喊“你到底爱不爱我”,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她那双疑惑的眼睛,也不断地追问我自己的内心。
但是我们依然相携相伴地走着,不知不觉中成为对方生命中的必然。代沟难以消除,血浓于水的纽带却不可断。明白这一点时我正在医院的产床上痛哭流涕。不难想象,以往手破个皮都耿耿于怀的我生孩子的表现绝对是令让人嗤之以鼻的。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10点,随着阵痛的加剧我基本上就是哭得一塌糊涂。医生护士烦躁地嘀咕:“见过会哭的,没见过这么会哭的”。唯一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一贯唠叨的母亲此时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病房到产房,她整整站了13个小时,我紧抓着她的手一直就没放松,根本没想着让她坐一会儿。只记得中途她跟我提过一句:丫头你松松手,我去吃点降压药就来。看我在疼痛的恐惧中根本没有理会她的意思,手抓得更紧,她也只好做罢。
在我儿子6个月的时候,我的函授学习进入了毕业考试和答辩的关键阶段,就是说这最后一次的面授我是无论如何要参加的,不然就要拖到下届复读,而且下届还不见得有我这个专业。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母亲开始收拾她和宝宝的行李,说“以前没坚持让你上学很可惜,现在就努力一下吧”。
于是我们祖孙三人推着婴儿车、装着尿不湿和奶瓶浩浩荡荡地上路了。3次换车,辗转5个多小时到达我学习的函授点。
那年的六月,气温早早地达到了36℃以上,我面授加考试的时间是整整10天。我在教室高度旋转的电风扇下仍然一阵阵地出汗,一是因为热,二是因为惦记抱着宝宝在街边整日游荡不能停歇的母亲。因为热,宝宝和大人一样烦躁不安,不愿意在招待所安心睡觉,执意要看路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和理发店门口旋转的三色招牌灯,母亲只好抱着他这辆车看到那辆车,这家理发店转到那家理发店。一次我中途跑出来给宝宝哺乳,远远地就看到宝宝在母亲怀里拼命哭闹,而母亲絮絮叨叨地哄着他,甚至抱着宝宝追着一辆红色的小车跑了好远。看见我她赶紧把宝宝递过来,说“好了好了,你再不来我都要哭了”。
炎热而郁闷的气温下,我看见她的脸红烫得像要滴血,脖子和胳膊上布满了黑且粗的痱子,有的已经开始溃烂。从那一年起,母亲年年夏天都会犯“粗大痱子溃疡”的毛病,非常痛苦和难受。每次犯病,她都会重提旧事,但是我知道,她从没后悔过。
渐渐地,我明白了爱与不爱都不是可以随便地用语言可以表达的。母亲年轻的时候眼神儿极好,年老了反而老花得比常人厉害。所以一幅眼镜总是低低地架在她的鼻梁上,读书看报织毛衣做针线都少不了它。但是有一件事情她总也做不好,就是给自己修脚。自然这件事就是我的了,每隔一个月我就得帮她清理一次钙化严重的脚指甲和脚底板堆积的老皮。对这个我是习以为常的,不认为有什么。倒是有一次听到邻居阿姨对母亲说,你女儿真孝顺,换我女儿倒贴点钱给她都不会干。母亲得意地说:这有什么?我养她这么大这点事情都不做,那还不是鬼在身上了!我听了只浅浅地一笑,没感觉有什么异样,我就是在尽义务。直到有一次,也可能新换的修脚刀太过锋利,也可能我急噪得动作大了一点,一刀下去,母亲嗖的一抖,母亲的脚底板被我连肉带皮地削去了一大块,血汩汩而出,我傻了,急忙用棉花压住,手心感觉到母亲的脚在抖。不一会儿血濡湿了棉花。突然地,我的心开始绞痛,浑身出满了冷汗,眼泪汹涌而出,抱着母亲的脚大放悲声。母亲很慌张,连声说,你别怕,我不怪你不怪你。我难过地说不出话,从那一刻起我彻底明白了,我是爱她的,很爱很爱,她受伤我会心痛,亲手伤害到她,我会痛不欲生。
同学聚会,一个青梅竹马的朋友言来语去间就有了一点点嘲笑:你丢不丢人,一把年纪了还不成熟,还跟小时候一样一口一个“我妈说”,你妈跟皇上似的。这无疑又是一声棒呵。是的,别人几岁就离家了,而我这几十年来几乎就没离开过我的母亲,我的生活中,生命中,甚至我的语言习惯中,她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母亲在哪家在哪,无论我走到哪里,只要是一回到她身边,就感觉是回到了家。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她生命里的主角呢?仔细想来,她为我做饭做了几十年不说,衣服自己来不及洗就扔给她,孩子没人带就让她“救火”,没钱买房子,她拿出了省吃俭用的积蓄一分为三,我们兄妹各得一份。每次外出,回来时总悄悄塞一件时装给我,她知道我经济紧张,喜欢那些东西却囊中羞涩。
转眼间母亲就奔七十了,头上的白发越来越多。她依然会唠叨过去的种种不如意,依然会埋怨父亲,依然会对我儿子说你再吃糖以后不到三十岁牙齿会全部烂掉。但是在我听来已经不那么刺耳了,因为她说的是实话,她头上的白发和脸上的皱纹说明了一切。她非要唠叨出来绝对是因为内心憋屈,并不是真的痛恨什么生活,而是渴望得到我们的理解。她对晚辈也不是漠不关心,而是运用了我们暂时不能苟同的方式方法。
因为白发多,所以爱美的她总是要求我帮她染发。每次,我都小心翼翼地打理着她的每一根头发,用黑得发亮的色泽去掩盖岁月留在她头上的白霜,然后为她做半个小时的脸部按摩。我做得很认真,仿佛在用心安抚她的不平,用爱带给她生命的色彩和活力。她也很惬意地享受着,似乎清楚地洞察了这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