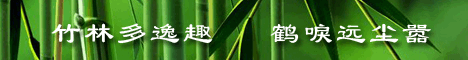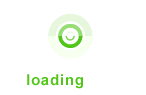利用一个周末假日,与几个死党相邀驾车同游庐山,早上四点多就出发了,大家一路上说说笑笑也挺开心,难得这么的放松愉快!到达庐山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放眼望去,只觉的这里风光虽然旖旎温润,但与众多的南方名山相比并未见的独具风姿。我便用另一种眼光去看待它,匡庐的独特之处不在于自然风光,而在于它独特的人文景观。
清末时,这里被划分为外国列强的租界地,因此大兴土木建了多种风格各异的洋楼别墅,在众山峰上争奇斗俏。上世纪初,蒋介石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喜欢上这来消暑避夏,匡庐因此得名“夏都”的美誉。
游庐山不累。行李甩在宾馆里,只需空着手闲逛,着实惬意。庐山的两大人工湖,一个是如琴湖,一个是芦林湖,湖光映着山色,美则美矣,可惜这“人工”二字,总让我觉得遗憾。游庐山,花径是不可不去的,花径石门两侧刻着一幅对联:花开山寺,咏留诗人。走进花径,其实就是游览纪念诗人白居易的主题公园。白居易的石像前面,一块巨石上刻有的——“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天天被八方游客象翻晒冬衣一样翻出来,我也一样硬是将这首七绝囫囵咽下以不负那位青杉上泪痕犹自杂酒痕的江洲司马。巨石后据说是诗人当年居住的草屋,我踏寻千年的诗踪,只见桃树无言,下自成溪,唐时的芳花千番开谢,游人的热情丝毫未减。
庐山上别墅有数百幢之多,而论名气绝对是美庐最大了,这幢本是一英国人赠送给宋美龄的礼物,据说蒋介石迷信风水,他认定此地是蛟龙出水的宝地,不过他万万料想不到的是,青龙一出水,赤龙便如潭。当年老蒋仓皇辞庙时,连孙中山先生亲笔所书“世界大同”都弃置不顾,可见其当年一败涂地的狼狈。此外美庐的旧主人还留下了两副宋美龄颇具水准的风景油画,不知江青看过心里是何种心情。
芦林一号也就是毛泽东同志的旧居,里面陈列的物品都是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原物。到处竖着“严禁拍照”的牌子,可我们还是偷偷地留下了一些“资料”,有卧室、休息室、浴室、会客厅,还有中央政治局会议厅。大红色的地毯铺就着条条通道,从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到简陋的浴池浴缸,一代伟人留下的痕迹无处不在。
仙人洞就在眼前。“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的诗句我已是久久沉吟,庐山的自然景观,除了瀑布之外,这仙人洞,是没有理由不知道的。可我面对石栏围起来的洞口,怎么也不能相信,心中不免一片惘然,是不是险峰我就不追究了,可眼前这一处,就是诗里的“无限风光”吗?岩壁上,一个天然石洞,开口不大,却被一尊吕洞宾石像占了大半。这里是吕洞宾的修仙之处,立个石像倒也不算什么。可石像两旁,还各自摆放着一个一米多高的青花瓷瓶,瓶里插着大把的积满了灰尘塑料花,前面神龛香案上也是插满了大小不等的香,香火正旺,烟雾缭绕。洞是天然的,可洞里洞外,人为的痕迹加上叩拜的身影,好好的一处景观,俨然成了香火盛地,仙人洞便因此沾染了人世的俗气。在我失望的同时,依然有人欢欢喜喜地焚香赞赏,不知道当年在毛泽东的眼里,仙人洞是不是现在这般模样?
游三叠泉,一路下行,全程有十余里,绝险处,只见脚底岚烟氤氲,游人如在云中漫步。原以为这就是李白笔下“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庐山瀑布,可友人说,三叠泉因为隐藏在重山深壑里,直到南宋时期才被人发现,并逐渐赢得了庐山第一景观的美誉。而当年李白笔下的“庐山瀑布”,水量渐少,气势早已担不上“三千尺”的美名了。
三叠泉,顾名思义,整个瀑布从山顶流经峭壁悬崖,分为了三叠,呈“品”字形,一叠飞落之后,分两叠再度倾泻而下,落入谷底深潭。泉瀑跌宕于山涯之间,哄然作响,激起水风透骨清凉。
范仲淹游庐山时写下一首《瀑布诗》,开头四句是:迥与众流异,发源高更孤。下山犹直在,到海得清无?不过最好的注解应当是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此刻庐山因三叠泉而变的格外生动。在人文的庐山和自然的庐山面前,我更偏爱后者,这种偏爱,让丰富多彩的庐山形象,更多地定格在那道飞流直下的气势里。
游含鄱口时,我们发现号称中国第一大湖的鄱阳湖简直太纤瘦了,若没有好眼力,还真不容易看见她的倩影。自然环境的破坏还远没到尽头,此地修建的那条长长的索道,上下的红色缆车犹如万绿丛中的“ ‘塑料花”,于周围千峦竟秀的景色极不协调。显然这又是那些利令智昏的主事者们的“杰作”。
庐山植物园背靠李白盛誉“庐山东南五老峰,青天削出金芙蓉’的五老峰,群山环抱,数千种植物中不乏珍奇品种。在园中,我们全都成了睁眼瞎,平时能叫出名字的植物似乎都自动消失了,穿行于林间小道,心想,植物学这一课,今生是再也补不全了。
庐山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原为唐代书生李勃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因李勃养一头白鹿,出入相随,人称“白鹿先生。”南宋朱熹任官到此地,复兴白鹿洞书院,自任山长,开坛讲学,江西学子文人就读往返此地可谓盛极一时。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天下书院之首”,这种说法让我等湖湘儿女很是不服,白鹿洞书院的历史虽更加悠长,但岳麓书院培养的经世济用之才影响却要更大,例如王船山,魏源,曾国藩,左宗堂等,人人都是能隔山打死牛的重量级人物,个个都名垂青史。雨中匆匆一游,连一副对联都没记住,见不到白鹿,也见不到道骨仙风的“白鹿先生”只看了一堆灰暗的砖瓦又有什么意思?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是苏东坡的遗教,但我还是愿意偷得浮生数日闲,住在庐山,享受大自然赐给的一席美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