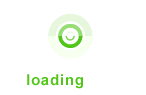离开北方有些时日了,来到这座南方的城市后,就一直在忙着絮窝,头发长了好长,卷卷的头发也有些直了,原来葡萄紫的彩发也变了颜色,于是利用周六上午,到新街口的超妍美容美发洗心革面,对于美化自己,向来不吝啬钱的。这儿一个长得高高大大、有点象当红小生陈坤的大工给我打理,他开口说话了:“小姐,你头发发质不好,很枯,用点好的染发剂吧。”好熟悉的乡音!忙问:“你是东北的吧?吉林的吗?”“你能听出来?!那你是北方人吗?怎么听不出你的北方口音?”我笑:“我是地地道道北方人,吉林人,普通话讲得还行,曾经做过二年的电台播音员。”于是,我们象多年未见面的朋友一样,聊北方,聊南方,付款时,他竟然自做主张的只收了我对折的钱。从超妍走出来,那浓浓的乡音驻在了脑中。
正月十五那晚去夫子庙观灯,回来的路上,竟然见到一辆白色凌志停在路边,车牌“黑AB0419”,当下怔住,左环右顾,以期见到车主,想必车主是北方人吧。等了有近二十分钟,不见主人归来,想想自己可笑,又摸了摸车身后,怅然而归。
原来同事的女儿在这座城市的审计学院读书,开学后给我捎来一箱刘老根辣酱,拿回家,全家人就因这辣酱,平日里蒸一碗米的饭还要剩下,而这顿,有先见之明的妈妈蒸了两碗米的饭还是没够。吃饭时,我手拿一颗大葱,蘸着刘老根辣酱边吃边说:还是家里的酱好吃。
与爱人在语聊室缠绵,要下网时,他说:给你放首歌吧,德德玛的《美丽的草原我的家》,随着歌声,竟然忘了今夕何夕,心飞回了我那此时银色的家乡。歌曲放完,半晌不语,他问:“怎么了?”“想家了”。躺下,一夜无眠。
爸妈来南方已很多年,他们乡音未改,所住楼区中,只要是听到讲北方话的人,就会问人家是不是东北的,哪管什么吉林不吉林,只要是东三省的,都是乡亲!但在北方的家中时,却分得很清的,吉林是吉林,黑龙江是黑龙江,辽宁是辽宁,即使同一个城市的江南江北,也感觉不那么亲。走出了原有的故园,在这南方的城市遇到故乡人,却大而化之,没有了地域之分,亲得胜过亲人:黑龙江的老乡把家乡捎来的粘豆包送过来,辽宁的老乡按照北方腌制酸菜的方法腌制好的酸菜送过来,妈妈把并不多的刘老根辣酱分成三份,一家一份送过去。
当我决定跳槽,离开央行的那一刻起,意识中只是对我视若生命的友情放不下,对那一个个曾经给我温情,给我关爱的鲜活的人舍不得,并没有感觉对北方会有什么留恋。那座塞北的小城与我今日居住城市的环境、经济、文化等方面是不可比拟的,为了追求那份生活的自由,灵魂的自在,为了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痛痛快快的活一把,更为了与已来到南方多年的父母团聚,我轻松的挥了挥衣袖,就哭着作别了北方的朋友,原本以为可以不带走一片云彩,却在又听乡音,再见乡车,又品乡食,再听乡歌中,就拔动了我的思乡愁。而这种思乡,由我那至亲至爱的小城已扩大到北方的一草一木,无不牵动着我的神经,渐至演变成一种北方情。
怎么能忘呢──那生我养我的八百里澣海,那妙音寺的钟鸣?!
怎么能不留恋──那第二松花江冰冻的江床,那泥石林的风光?!
怎么能不梦回──镜月潭的雪场,格林梦的水乡?!
…………
不经意间,轻挥的衣袖中,带走了全部的云彩!北方已深深融入了我的血液,我的情感,我的灵魂中,如影随形。在这结局才看透的黎明,我遥望着北方的星空,终于明白:北方,是我今生今世挥之不去的那抺乡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