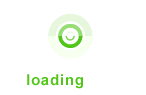小时候住在清明桥旁舅舅家时,那陡直的小土坡,那茂密的翠竹林,在我和伙伴的眼里是有着无穷乐趣的,那是我们的嬉戏地。单单是草丛中那嫣红的"蛇莓",已是无尽的话题。老人说那是蛇下的蛋,那红色的果实在闪烁,吸引的永远只是好奇、探究却忐忑的目光。这是个永远的谜,想尝一下,终于没有勇气。直到今天,看到这种植物,还是会浮现出小伙伴你推我让,谁也不肯去摘的场景。
记得春天可采摘刚发的竹笋做汤,摘"草头"做翠绿的清明园子。炎炎夏日,小河涨满了水,蹲在河沿就可以耖虾,晚饭大人就有了下酒的菜。我也尝试过在午睡时溜出去,拿着家里淘米竹箩捞小鱼。小鱼自然不会甘心被捉到,我一心急,使劲一扑。鱼是捞到了,人也跌入水里,小伙伴们你拉我拽,把我从河边"捞"起,鱼儿自然溜之大吉。自己则湿漉漉地爬上岸,揪着裙摆灰溜溜地窜回家,还不忘威胁邻家的姐姐不许告状。
那时烧饭大多都用灶,学着舅妈的样子,我把炉膛里添满柴草,点燃纸迅速扔到炉膛里,柴草被火焰吞噬了,浓浓的烟四处逃窜,呛着我满脸通红,拿着那把破蒲扇扇风,呵,这可是体会到了煽风点火的气势了。炉子问题解决了,架锅、煮饭、炒菜分工明确。那时我只会煮饭,哥哥倒是有大厨的风范,青菜洗净,等锅热了,倒上半勺油,菜就下锅啦。锅铲左右翻炒,不小会儿菜已成深绿色,加点盐,就起锅了。看着哥哥忙前忙后,我的心也痒痒的,操起了饭勺在米饭锅里上下搅拌,一会儿火大了,就把柴火扒出一些,一会儿火小了,又忙着添柴,渐渐水分蒸发了,香喷喷的米饭也做好了。品尝着自己动手做那或淡或咸的菜,那干脆焦黄的锅巴,心里美滋滋的。
现在想来,那份天真,总是太短太快,只是人生的一瞬,已经走远。只留在心中的某个角落,只能在某些特定的时候,经由某些事情一次又一次得被唤醒。
------